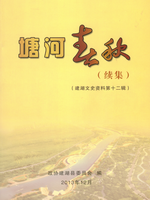“大跃进”年代的那些事儿(朱明安)
凡经历过“大跃进”年代的人,脑海里都会留下一个难以回首的印象。那是因为1958年“大跃进”运动,我们党在探索走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遭受的一次重大挫折,犯了“左倾”冒进错误,教训非常深刻。
建湖县和各国各地一样,在连续三年的“大跃进”中,刮起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给建湖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农业持续减产,工业遭受破坏,人民缺吃少穿,因饥饿和营良不良造成浮肿病、消瘦病、青紫病等大量发生,人口出现了负增长,国民经济处于极为困难的严重局面。这里仅举“大跃进”中的一些实例引以为戒。
一、不切实际的舆论导向
脱离实际的舆论宣传,是“大跃进”年代大搞群众运动,造成狂热氛围的一种独特现象,也是“五风”中“浮夸风”刮起的源头。
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打击了一大批敢于说真话、干实事的同志,因而在“大跃进”“左”倾冒进运动发起后,许多人随波逐流,跟着说瞎话,党的报利也随之推波助澜,屡屡发表脱离实际的虚假报道。1958年麦收,河南省遂平县一位在卫星农业社抓点的副书记,按照当时从中央高层到地方各级普遍认可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时髦口号,“大胆”地将一块亩产只有四、五百斤的小麦浮报为亩产2105斤。6月8日,《河南日报》和《人民日报》作了报道,放了全国第一颗高产卫星。7月23日,《人民日报》又报道了河南省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亩产7320斤,还发了号外。8月13日,《人民日报》分别报道了湖北省麻城县溪河乡和福建省南安县胜利乡早稻和花生高产,亩产达到3.69万斤和1万斤的巨大卫星。从此,竟放高产卫星的报道不断增多,最高亩产达到13万斤。建湖县在这股歪风冲击下,也在8月6日县委办公室编的《大丰收喜报》首期刊出了4颗早稻高产卫星,他们是:塘东农业社2亩“早沙粳”亩产2672斤;近湖社1.5亩早稻单产3500斤;连吉乡亩产4263斤和秉文乡新河社一队1.1亩“中农四号”亩产突破6000斤。9月25日,东风人民公社(今近湖镇)放出1.1亩中稻 “绍景籼”亩产11976斤的大卫星。群众听到广播都十分惊讶,“绍景籼”是个土种,产量再高也难突破600斤,真是世道变了,公鸡能下蛋了。尔后,亩产13000斤、14500斤、20000斤乃至更大卫星,陆续在《大丰收喜报》上出现。
这年秋,县委第一书记成豫华亲自蹲点抓上冈区(今上冈镇)同心社的万斤试验田,中共盐城地委在此专门召开了现场会,组织全区参观学习,还向省委和中央作了报告。时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根据毛主席指示精神,不止一次地写信给盐城地委书记陈宗烈,了解建湖和其他各县种试验田的情况,询问争取水稻亩产5000斤,甚至争取一、两处达到万斤有没有这个可能?陈宗烈复信写道:从建湖县第一书记成豫华亲自搞的一块万斤试验田,结合上冈区委一块1.1亩试验田的密植情况看,亩产万斤是有把握的。其实这些高产卫星是假的,有的是通过“并田移苗”方法伪造出来的,也有的是找出一、二株长势特好农作物收获量乘以大田密植株数推算出来的。
报刊失真报道和各地浮夸典型介绍,造浓了农业生产“大跃进”氛围,一个放卫星,夺高产,表决心,挑应战,报喜、贺喜夺冠军的狂潮掀了起来。6月底,盐城地委在建湖召开夺取秋季更大丰收现场会,县委书记成豫华作了《干劲百倍,水稻双千,摆擂台,夺冠军,乡乡社社上北京》的发言。随后上冈、近湖、辛庄、恒济等12个乡和红旗、高马、前庄等23个农业社站出来摆下高产擂台,相互挑应战,县直机关也向东台、常熟、崇明三县发出了倡议书……地委领导在大会总结时,表扬了建湖的典型放得好,号召大家要学习先进,解放思想,做“神仙”不做“凡人”。
地委现场会后,建湖县召开全县党员大会,与会同志听了动员报告后,觉得压力很大。但有话不敢说,硬着头皮把各自的试验田亩产指标定到1万斤、2万斤直到4万斤,写下了放卫星的决心书。秉文乡委书记姚俊嵩,带着一份《鼓冲天干劲,夺亩产万斤,中南海赴宴,怀仁堂谈心》的发言稿,满以为在县里发言能一鸣惊人,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芦沟乡蹲点的县委农工部长许长华作的《革命加拼命,亩产方万斤(四万斤)》发言,使姚书记的发言稿未出笼就“卡壳”了。时任秉文乡党委秘书孙善夫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那年头当秘书是个大忙人,也难做人,整天在领导的旨意下违心地拟报告,写战书,发倡议,编假造谎,信口开河,真是心思挖空,大话说尽。”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豪言壮语也出尽了风头。就在全县党员大会后,从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到农村各个角落,用彩纸写成的诸如“大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脱去一层皮,苦战八十天,夺取水稻亩产过双千”等大标语随处可见,墙壁上开辟的《宣传栏》、《墙头诗》,包括贴出的决心书、挑、应战书,上面的豪言壮语比比皆是,连过1959年春节,群众的大门对联也写上了豪言壮语。请看1959年2月县委召开第二届党代会的工作报告是这样描述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形势的:“……冬天是‘心热不怕天寒,人齐不怕地冻’、‘头顶满天星,脚踏三寸冰,雪花飘飘干千斤’;春季是‘大跃进大干一场,齐动手一刻不让’、‘春雷一声响,猛虎下山岗,苦干加巧干,打胜第一仗’;夏季是‘上场一担麦,下田一担秧,来去不脱空,跃进之中当英雄。’上冈乡有些秀才形容夏季生产场面说:田边撑军帐,田间是战场,连营几十里,号角震天响,战旗蔽日月,灯火映天红,粮帅升宝帐,今古实无双;在秋季大搞深翻秋播,实行三化、六定、八到田:圩埂是牙床,稻草是被更,工具是刀枪,就用这股冲天劲,痛痛快快干一场。炼钢的人们同床铺分家,和高炉作伴,汗水当铁水,炼钢又炼人” 。
二、农业“大跃进”中的苦干与生产上的瞎指挥
“大跃进”首先是从农业开始的。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以粮为纲”的口号,要求五年、三年甚至一、二年达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指标。建湖县为实现当年粮食总产6亿斤,皮棉总产224万担的奋斗目标,发动农民群众以“愚公移山”的意志日夜苦干和“敢想敢干”的精神盲目蛮干,不断创造农业生产的“奇迹”。
1、积肥。大搞绿肥向海陆空进军。从1958年麦收开始,把河、沟、塘中的水草捞光,水里不见绿;地上长的青草连草皮铲光,陆地不见绿;树上的树叶抹光,空中不见绿。有的索性把树锯倒,推入河中,泡成黑水,车水灌田,称之“水肥两用,一举两得”。冬春积肥,发动中小学生拾稻根,把麦田中的土块垒成小窑,点燃稻根薰土块。还组织群众铲锅膛土,搞颗粒肥、人造粪、三鲜汤等,谓之“造肥”。
2、深翻。秋收秋种时全面展开,块块深翻,一亩不漏,谓之“改良土壤”。深翻深度一般为1~1.5尺,不少的在2尺以上。秉文乡水田最深挖到5尺,底层垫柴禾,中间插稻草,上层覆泥土,结果成了不好耕作了“弹簧田”。深翻的麦田因为表层是死泥块,不好耙碎下种,就组织群众点麦。
3、密植。是当时浮报产量放卫星的普遍栽植方法。插秧要求:卫星田每亩100~200万株,高产田80~100万株,一般大田60~80万株。种麦下种每亩100斤左右,有的下到200斤,造成种子严重浪费,结果苗密发黄,便组织人工间苗或用耙子划,称之“替麦子梳头”。
4、工具改革。1958年春,县委发文提出丢掉一条辫子(水田拉犁辫子),消灭两个挑子(积肥、水利用肩挑),实现四化(耕地绞关化,运转工具轴承化,收割脱粒半机械化和提水工具新式化),还规定了奖励办法,鼓励创造发明。随后,全县各区乡把木匠、铁匠等手艺人和懂技术者集中起来搞技术培训,边干边改。还根据县委“自力更生解决原料问题”的指示,令群众伐木倒树,拆风、洋、脚车,除门板、砧板、献棺材料子等支持工具改革。据1958年4月11日统计,全县仿制、改制、发明创造的新式工具40255件,当时认为成功的有绞关耕地机,运泥翻斗车、脚踏脱粒机、吊土机以及布肥器、棉花六行点播器等,而绝大部分无实用价值,浪费了大量人力和原材料。
5、搞“河网化”。群众习惯称“挑生产沟”。“大跃进”时期组织农民整田开沟,实施河网配套建设,为保证农田旱涝保收和农业丰产丰收,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当时也有不少不顾主客观条件,缺少合理长远规划,被挖成废沟废河的。如“大跃进”开始的1957年冬,开展以水利建设为龙头的冬季大生产运动,县委在钟庄乡搞“河网化”试点,把40多部风车拆了搭浮跳,20多条农船装满泥土沉入河底当坝基,调集8000多男女劳力挑“跃进河”。工地上办起了食堂、卫生室、托儿所等。拆腾了一个多月,“跃进河”却因计划不周而半途停工,挖废了大面积耕地,破坏了大批农具,开创了生产瞎指挥风的先河。
三、大办工业,“大炼钢铁”运动
在农业“大跃进”的同时,工业“大跃进”也迅猛开展起来。建湖县根据党中央确定的工业“以钢为纲”的方针和“大力发展地方工业”的指示精神,按照盐城地区工业会议的部署要求,大办乡社工业。通过平调方式,集中大批人力、物力,兴办机械、轻工等加工工厂,创办工业区。据1958年底统计,全县兴办县、乡、社大小工厂835个,其中初具规模的有621个,基本上每个公社办起一个工业区。联星人民公社(今芦沟镇)在大崔庄东首创办了工业区,召开公社成立大会的那天,数十条装满砖瓦、毛竹、木料、机械等物资的大船开进了大崔庄,熙熙攘攘的参加大会群众抬着织布机、缝纫机、织袜机等,挑着粉坊、糖坊、油坊工具涌入会场,向大会报喜,支持大办工业。工业区拥有轴承、锯木、水泥制品、土制化肥、毛巾、丝袜、服装、轧花、造纸、油米加工等新办厂36个,新建厂房228间,职工2000多人。这些厂由于盲目兴办,设备条件差,土法上马缺乏技术力量,加之销售渠道无法解决,虽然干得热火朝天,但不到一年就冷落下来,最后只好把全区工厂合并成一个综合厂。
在全民大办工业中,一马当先的要数“大炼钢铁”运动。为了保证“钢铁元帅”升帐,1958年8月27日,建湖县开始办起县乡炼铁小高炉,并根据地委指示,于9月中旬组织500名青壮男劳力,组成钢铁远征军,赴南京大厂和江宁青龙山采矿与炼铁,为县内提供大炼钢铁原材料和技术。10月份以后是大炼钢铁的高峰期,计办大小高炉280座,出铁270吨、钢75吨。10月28日,县组织大炼钢铁大会战,集中在县人民体育场,按炉群举行誓师大会,县直机关干部、企业工人、城镇市民和建湖中学共7200人参加会战。152个土高炉相继点火,只见县体育场人如潮涌,烟火冲天,机器轰鸣,各公社组织的文工团也到现场演出助威。经过24小时激战,县大炼钢铁指挥部传出捷报,一天产铁30.8吨,超过原来25天产量的总和,放了大炼钢铁以来最大卫量。
为了支持全民大炼钢铁,全县开展村村户户献废钢铁活动,个别地方号召群众买新锅,砸旧锅,无偿捐献支持大炼。把乡村中的大批树木锯倒,作为大炼钢铁的燃料,加上农业“大跃进”的乱砍滥伐,所剩树木无几。到了冬天,举目远望,空旷的原野上,只有几棵孤零零的树木在寒风中摇曳,显得十分凄凉!而这些小高炉炼出的钢铁,含碳量严重超标,有的仅成了废品。
四、人民公社化刮起了“共产风”
人民公社是在“大跃进”的热浪中建立起来的。1958年8月底,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动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下发了《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全面地展开。建湖县紧跟形势,在其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先后成立了东风、上游、火箭、联星、巨人、威武、燎原、红旗、灯塔9个人民公社,全县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对于成立人民公社,当时从中央到地方,都认为是农业“大跃进”的有效组织形式,是我国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雏型和基层单位。因为他的基本特点,用毛主席当时话说“一曰大,二曰公”。所谓“大”,就是规模、权力大,生产和生活资料可以按需调用;所谓“公”,即实行供给公有制,由公社统一核算和管理。因而在社会上流行着“人民公社是通往共产主义的金桥”、“共产主义离我们已经不远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和“吃饭不要钱”等说法。由于对人民公社性质和实施过程中存在“左”的倾向,引发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建湖县也深受其害。
1、调集劳力,搞突击会战。公社成立之初,按生产片(邻近的几个生产大队结合而成)或重点工程(如“河网化”工程)成立会战工区,调用的男女劳力以军队建制编成大队、中队、小队等,集中劳动,集体生活,统一调度指挥,还制定了作息时间表,谓之“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1958年10月,毛泽东发出“大办民兵师”的号召后,这些工区组织就变成团、营、连、排、班民兵组织了。所集中的劳力吃住在田头、工地,后勤保障也跟进到现场。联星人民公社按工区会战实际,实行“六定”(定阵地、定任务、定规格、定时间、定报酬、定纪律)、“八到田”(住到田、吃到田、医疗到田、农具修理到田、学习到田、评比到田、文艺宣传到田、托儿所办到田)制度,在全县作了推广和仿效。为鼓舞群众斗志,营造会战氛围,成立用古今中外英雄人物命名的专业队,如“黄继光突击队”、“花木兰战斗队”等。1959年春耕生产和夏收夏插,上工哨子一吹响,各个专业队扛着自己的“帅”子旗一齐出工,一起奋战在田头、工地,样子十分气派。有的地方在工地搭起宣传台,装上高音喇叭,没日没夜的喊话,放革命歌曲,宣传会战中的新人新事。红旗人民公社(今钟庄社区)别出心裁地雇了一只大船,载着十几名文工团员,在东、北、西塘河游转,吹拉弹唱,鼓乐齐鸣,通宵达旦,以势压邻。然而这些会战,往往顾此失彼,丢下到手的庄稼不收,该干的活不干,遗误了农时,糟塌了庄稼,得不偿失。
在大会战的日子里,农民在“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口号下,以“大跃进”的姿态,没日没夜的大干苦干,一天能完成几天量的活,打早工,干夜活是常有的事。有些生产队长天没亮就喊群众上工,走到社员家门口,一声狠、两声吼、三声不动就动手,一脚踹开门,把人从床上拖起来,强迫上工,群众称之为“三声队长”。在那时,为了完成会战任务,干部打骂社员,强迫命令的事时有发生。
2、平调物资,积极“大办”。人民公社建立后,大办公共事业的事很多,如大办工业区、大办养殖场、大办农业中学等等。这些大办工程所用物资,特别是建筑材料绝大部分来自民间,出现了滥拆庵堂庙宇和社员房屋的现象。联星人民公社创办联星农业中学,拆掉夏桥大桥杨湾自然村37户社员房屋110间,盖教室60间,食堂、保管室、小卖部16间。1958年秋后,县委提出发展集体化养猪,发动社员个体猪一律折价归队饲养,群众有反感,一度出现了偷卖偷宰生猪的风潮。年底前,全县办起了16个集体畜牧场,先后从外地购进苗猪57000多头,由于运输、饲料和管理不善,导致瘟疫流行,一下子就死掉23100多头,占购进数的40%以上,芦沟畜牧场一天就死亡900多头,东风公社杨楼大队集体饲养的300头苗猪也全部报销,群众见状,十分痛心,有的当场哭了。
3、搞居民点,办公共食堂。建立农村居民点是在“建设共产主义新农村”的口号下进行的,也是人民公社实行“生活集体化”的一个重要方面。1958年入冬之前,全县试建新农村居民点,决定以生产大队或生产队为单位,把零散在中心村庄周边的农户,强行集中安插到庄内居民的附属房屋内居住,以利集体化行动和管理。被迫搬迁的农民,眼睁睁地抛弃了自己的住房和坛坛罐罐,带着妻儿老小和几件大宗用具,依依不舍的离开了故居,挤进了“新居”。而“新居”的房东,很不情愿地接纳这些外来之客,因为乱轰轰的环境,打破了他们恬静的日常生活规律,弄得大家怨天忧人,怨声载道。联星公社夏桥大队杨湾生产队有的搬迁户还算幸运,被安排在大队大食堂顶头的房间内,6间分住8户。虽然居住拥挤,但吃饭方便,也不缺房东的情。1960年春,原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殴阳惠林到这里视察,称夏桥大队食堂是世界上最大的“麻雀笼子”。搬迁户留在原址的旧居,房屋结构质量好的被拆除支持“大办”,质量差的大门常年上锁,任凭风雨摧残。据县1962年清算平调退赔账目显示:全县拆调房屋计15207户、34379间,分别占比15.2%和15.63%。
提起办农村公共食堂,人们自然会想到这是“大跃进”年代的事,因为它最能体现人民公社“生活集体化”的特点。据全国党史文献介绍,至1958年10月底,全国农村建立公共食堂有265万多个,在食堂吃饭人数占农村总人口的70%~90%。建湖县从1958年10月起办起农村公共食堂,一直延续到1961年夏。在当时“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的口号影响下,开头几个月,用粮无计划,吃喝加浪费,毫不悯惜。可是到了后来,发展趋势就越来越不尽人意了。1959年春节一过,食堂就按人口、按劳力、按计划打粥打饭菜,虽说吃的不好,但还能吃饱,到了下半年,口粮就实行低标准、“瓜菜代”了。1960年,人均口粮标准降低到每天只有五两六钱(折合现制3.5两),公共食堂每一只能供应三餐稀薄粥,有的连三顿都供应不全。群众形容稀粥是“粥汤看到碗底,一碗找不到几个米”。庆丰公社联合大队只有一个公共食堂,263户社员吃饭打饭很不方便,靠食堂半里路内的有62户,半里到1里路的有140户,1~2里路的有39户,2里以外的有22户,途中要经过一、二道木桥。到了雨天,因路滑难走,拨饭粥下河和人掉下河的事常有发生。群众对吃食堂有反感,说吃食堂有三多:吃冷粥冷饭生胃病多,两头冒烟烧柴草多,打饭前后拥挤打盆泼粥怨气多。由于口粮低标准,因饥饿造成浮肿病、消瘦病、青紫病和妇女子宫下垂病大批发生,最高峰达40500多人,人口死亡率远远超过出生率,是我县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经济出现最为困难的历史时期。
转自《建湖史志网》
- 上一篇文章: 从军粮供给看新四军后勤保障系统的廉政建设(周浪野)
- 下一篇文章: 一场难忘的演出(陶柱)



 站内搜索:
站内搜索: